残疾军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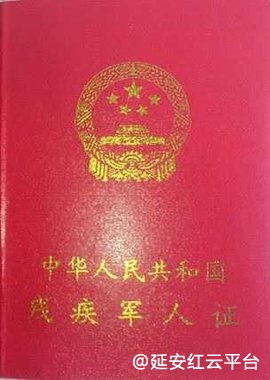
我有一本国家发的残疾军人证,上面写着“残疾等级八级”,“残疾性质因公”。每当看到或想到“因公”两个字时,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就会浮现。
上世纪70年代,为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支援陕北老区农村建设的号召,陕西省军区组织军区机关和独立师干部分批赴延安富县支农。我是1975年6月至1976年7月到牛武公社牛武一队支农的,当时我在独立师五团政治处宣传股任干事,同去的还有团司令部参谋王天锡和排长赵生有,我是组长。
支农工作队进入农村后,按规定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住的土窑洞,吃的轮流派饭,艰苦奋斗搞生产,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不怕苦,二不喊累,一心一意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时间一长,社员们也都把我们看成是自己队里的人,对我们充满着信任和希望。
支农期间值得回忆的往事许许多多,那天所遭遇的一场马惊车翻的事情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1976年3月的一天,我同社员一起往坡垄地送肥,使用的主要工具是单轴双轮架子车。这种车在北方农村很普及,生产队里许多社员家里都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架子车的车厢和车轮不是固定的,用时把车厢底部的卡窝架在车轴上,不用时把车厢靠墙上,车轮扛回家。因往坡垄地送肥,上坡难,就用了队里的马和骡子,由一人牵着,牲口脖套上引出两条绳子掛在架子车两边,架子车由一人掌辕、两三人推。那天我一直掌辕,到了中午饭时,我拉着空车往回走,一个姓雷的社员(记得他是个十六七岁的后生)牵着马说:“刘干事,我把马绳掛上吧,这样你不累”,我说:“不用了,空车不累”,他又说:“马闲着,掛上吧”,我就没再推让。
那时我们回村的路是正在施工的一条公路,刚铺了一层拳头大小的基石,架子车不停地颠簸。刚走了十几米,拉车的马突然惊了,拼命向前奔跑,我第一反应是“把绳子抓紧,别松手”。小雷使劲拉着惊马,但缰绳还是脱手了,我被惊了的马拉着同架子车一起奔跑,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比较冷静,想立刻坐到车厢上,伺机跳下去。就在此刻,因颠簸使车轮和车架分离,车架将我压倒,我双手紧握车辕,前身贴着地面,后背背着无轮的架子车厢,被惊马拖着在布满尖石的路面上行进,社员们此时也惊呆了,有的追赶,有的急呼。
被马拖行几十米后,突然看见对面走来一社员,我即刻高呼:“把马拦住”,可惊马绕过来人继续奔跑且速度更快。
“怎么办,怎么办”,本能的呼喊声如霹雳一样使我恍然淸醒,此时的大脑变成浩瀚的夜空,几个闪念如流星划过——“一是不要慌,靠自己救自己。二是决不松手,架子车底有几根方横梁,如松手横粱从头顶划过,后果不堪。三是惊马肯定奔向马厩,途中有两道旧水沟,必须在过沟前自救”。冷静和自信使我急中生智,我把右手移到车辕下端,试着向上举了两下,随后用尽力量推举,车架与地面形成三四十度夹角,我迅速向左翻滚。
成功了,成功了!惊马拉着车架继续奔跑,我躺在路面上。虽然已过去四十六年,当时躺在路面上的姿形和心境我记忆犹新。
“静静地躺在松软的棉被上,仰望着蔚蓝的云和明亮的太阳,喃喃自语,我活着,我活着,华宁,你真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追赶的人们到了身边。大家扶起我后才看见军衣的三个扣子已不见,皮带扣上的铸纹已磨平,双膝外的军裤、绒裤、毛裤和线裤已磨透,双膝多处破伤,血正在流。大家把我送到公社,支农的我团军医张捧相给我做了清创和包扎,当时公社无X光机,只能吃药静养。团里负责大队支农的刘振山教导员和战友及许多社员都来看我,还享受了“病号饭”。那个姓雷的小伙来了好几次,每次我都安抚他几句。
由于农事正忙,我只休息了三天就慢慢迈步到田头干些轻活。回到部队后,经多次检查确诊为双膝创伤性关节炎,右膝软骨和半月板损伤。经治疗,走路、跑步功能逐渐正常但不能下蹲,蹲下后须靠双手的拉力才能起来。从那次受伤后,我走到任何地方如厕时都先寻找坐便器。后来经过部队医疗卫生和有关部门鉴定,评为八级残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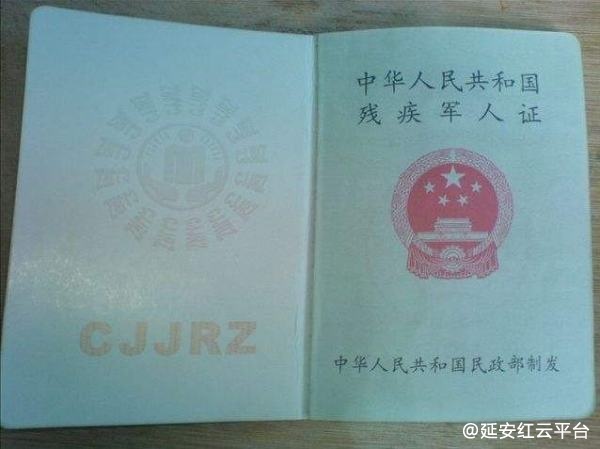
得到“残疾军人证”已经三十多年了,我珍惜它,因为它是我从小就有的“自信”的佐证和续延,“自信”陪伴着我的军旅生涯和人生道路。每当因它而获得优扶时,会生出宽慰和谢意。我珍惜这本“残疾军人证”,它在我心中是一本生命之花的相册,一首终生怜爱的诗歌。
(编辑 何利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