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共同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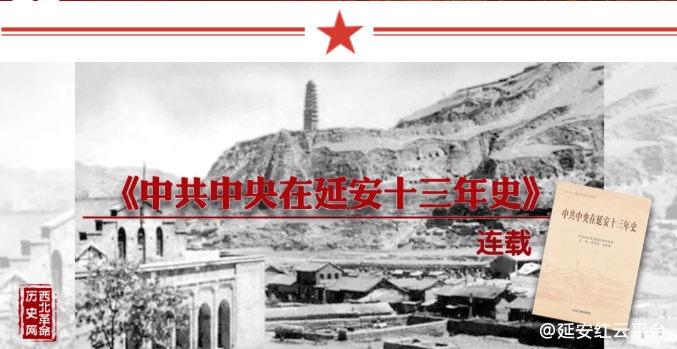
中共中央在争取东北军和张学良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争取和团结工作。
杨虎城出生于陕西蒲城县,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并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很早就与共产党建立了关系。1923年他在陕北榆林养病期间,结识了在榆林中学任教的早期中共党员魏野畴,并从魏那里对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中国政治形势有了一定的认识。此后杨虎城一直或明或暗、或断或续地与当地的共产党有着一定的联系,杨所属的部队甚至被誉为“共产党的仓库”。共产党员南汉宸深受杨虎城的器重和信任,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曾特别委任南为政府秘书长并代他主持省政府的政务。尽管后来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过一些波折,但从未改变对共产党的正确认识,正如他所说:“共产党员不怕死、不贪财、能干事、有献身精神,所以,我要用他们。”1927年秋,杨虎城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做一个贺龙”,并与共产党员谢葆真结了婚。在蒋介石下令“清D”反G的压力下,扬虎城将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礼送出境”;下令释放过被捕的红军将领刘志丹,甚至与红四方面军确立了反蒋抗日、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
1933年春,蒋介石免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邵力子接替。1934年,南京政府把孙蔚如第十七师四十九旅改编为新五师,调防河南,脱离杨虎城系统,划归刘峙统领。随后,中央军、东北军陆续开入陕甘,不仅经营西北的计划受挫,而且杨虎城开始面临着被蒋介石或东北军吞并的危险。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G”内战,却损失惨重,部下怨言颇多。杨虎城空有发奋图强、改弦更辙的抱负,但却束手无策,这些都让他的心情十分苦闷。为了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意愿的杨虎城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在到达陕北后,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做争取与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共同抗日的联络和准备工作。
南汉宸、申伯纯联手争取杨虎城 1935年10月,在北方局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南汉宸联系到同为杨虎城旧部的申伯纯,申曾长期在党的外围工作,有革命的热情。接受南汉宸的任务后,申伯纯于11月初赶往南京,见到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转达了南汉宸对杨的问候,并向杨宣传了中共的《八一宣言》精神,杨虎城对中共的主张表示赞许,并希望从南汉宸处得到中共关于联合抗日的具体办法。了解了申伯纯与杨虎城会面的详细情况后,南汉宸急忙向北方局进行了汇报,并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以个人名义再度委派申伯纯向杨虎城提出了合作的六条办法,主要内容是: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掩护往来人员;协助红军购买急用军需;择点建立秘密交通站,加强联络,便利来往交通。临行前,南汉宸特意叮咛申伯纯:假如杨虎城同意这几项条件,或者有所修改补充,中共北方局将另派专人前往商谈,并由派去的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关系。1935年12月中旬,当申伯纯在西安向杨虎城转达了南汉宸的几项建议后,杨表示基本同意。鉴于当时中央代表汪锋已开始和杨虎城取得了联系,为了稳妥起见,杨没有在第一时间对申伯纯作具体答复。
汪锋密晤杨虎城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委派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成员、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去西安面见杨虎城,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联系、谈判,争取联合抗日。1935年12月,在汪锋出发前,毛泽东与汪锋谈话指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会有全国的大联合。要求汪锋“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信中对他“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表示“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信中还以“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的语句,激发杨虎城的抗日爱国热情。
汪锋与杨虎城会面后,陈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杨虎城随即提出三个问题:(一)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杨称,孙蔚如部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往来。但受到过红四方面军的无故攻击,所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二)十七路军警备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杀害了张汉民,对此,他本人也非常不满。(三)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汪锋对这三个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尤其是关于张汉民被杀一事,汪锋解释说: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中共党员,现在中共中央已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十七路军说来,当然也是一个沉痛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关于提供帮助的问题,汪锋解释说:今后双方如果不互相攻击,就会互不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中共方面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
王炳南回国争取杨虎城 1936年春,共产国际找到了杨虎城的世交好友王宝珊之子王炳南,让他回国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是陕西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杨虎城资助他去日本留学,后又去了德国。王炳南在德国时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等职,与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关系甚好。季未特洛夫给他的任务是:劝杨签订和中共的互不侵犯协定,停止内战,共产国际允许通过新疆给杨虎城帮助。王炳南自知身份特殊,接受任务后于1936年4月回到西安。杨虎城见到王炳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到西安,高兴地说:我已经与中共某些人接触过,可是毕竟素不相识。现在你回来就好了,可以无话不谈。王炳南将季米特洛夫的话转告给杨虎城,杨听了非常高兴,两人彻夜交谈,更加坚定了杨虎城和中共合作的念头。杨虎城遂即将王炳南留在十七路军,还让其和张学良在上海的好友杜重远联系,后让王炳南去拜访张学良,由此加深了张杨的联系。王炳南回忆称:“我到西安见到杨虎城,他很高兴,认为我是国际派来的人物,很重要。他和张学良都想拉上国际关系,得到国际的帮助。张学良就曾说过他要派代表到欧洲去找国际关系。我和杨虎城谈的很顺利,没有不同意见。”
王世英与杨虎城密谈 尽管杨虎城一直与共产党人合作不断,但却从未与中共中央发生过直接的关系。汪锋的到来和毛泽东的亲笔信,使杨很感意外。但是,由于此前对汪锋并不熟悉,本着一贯沉稳的作风,杨虎城对来人和来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此,在留汪锋的同时,杨立刻派人秘密赶赴天津,找南汉宸要求再派人来西安会谈。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代表王世英(王曾在杨部工作过,杨知道他的党员身份)来到西安。
王世英见到杨虎城后,首先证实了汪锋的中央代表身份,并在随后的会谈中,与杨达成以下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十七路军签订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第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3月,王世英向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同意王世英和杨虎城商定的各项原则。4月,王世英到韩城再次与杨虎城会谈,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6月,杨虎城在富县和西安分别设立交通站和运输站,加强同中共的联系。
中共领导人对杨虎城的期望原本要高于张学良,因为杨毕竟与中共交往颇深,加上同蒋介石矛盾的加深。因此,中共曾经公开谴责过阎锡山、批评过张学良,但却并没有对杨虎城使用过指责之词。尽管中共中央采用多种渠道,多次派人团结争取,但由于杨虎城对共产党以往的误解和顾虑一时难以消除,因此犹豫不决,对中共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倡议半就半推。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称赞杨“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但是,对于杨“为友为敌,无明确之表示”和“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的情况,表示了不满和失望,在明确了“敝方(将)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后,表示将“派张文彬通知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9月3日,毛泽东致信十七路军将领孙蔚如,希望通过孙蔚如从中斡旋,双方取消敌对行动,称:“贵我双方彼此接壤咫尺,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贵方民团与敝方游击部队,彼此负责约束,不使再生误会。”
经过反复努力和不懈争取,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终于逐渐密切起来。12月5日,毛泽东就联合救国之大计及给予红军给养援助等致信杨虎城:“有数事奉商于阁下者: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之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复次,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团结巩固士气甚盛。然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叨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还期约明年三月,决不失信。另备轻机关枪一百挺,如兄处需此,敬以奉赠。复次,尔后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复次,空间通信再不可缓。承允即立实行幸甚,某君另有任务,兹重选一人,携带密码呼号,随李君来尊处。从十二月十五日起,重要机密均经电报交谈。”至此可见,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三位一体”统战局面的形成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地盘意识相对强烈,面对突然开进当地的20余万东北军,他内心十分矛盾,既赞同幕僚对“东北军有抗日情绪、张学良和蒋介石有分歧”的判断,也担心东北军受蒋愚弄,联合蒋系部队向十七路军施加压力。
张学良刚到西安时,自以为受过教育,见过大世面,兵多将广,跟蒋介石有着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因此,张根本不把杨虎城放在眼里,在杨的面前不仅是一副长官架势,而且私下常以“老粗”称之,两人关系极不融洽。而东北军初入陕甘,对西北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不甚了解,双方之间缺乏信任,彼此尊重不够。加之东北军的带队军官们自以为兵强马壮、武器精良,既看不起红军,也看不起十七路军。在日常生活的琐事方面,东北军总是表现的骄气十足,在看戏占座、街头争路等问题上,经常挑起事端、打架吵闹,甚至拔枪相向,言语态度,给人以不好印象,双方少数部队,因驻地靠近,有时还出现相互警戒的情形。
蒋介石也害怕张、杨二人结盟,所以派特务散布谣言、火上浇油,说什么张学良失之东北,有取西北而代的图谋;当时,东北军正准备在西安周边购地建房、安置家眷,这些行为似乎无不验证了类似的传言,十七路军和杨虎城的疑虑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后,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虽然公务交往频繁,但在很长时期内,双方都是官样应酬,“内心话都不肯说”。这样敌对的日子久了,仇恨情绪慢慢传染到了中上层军官,问题似乎正在趋向恶化。张、杨都长期带兵打仗,久经战阵,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张学良为了消除误会,避免冲突升级,曾经派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向杨虎城做工作,但收效甚微。迫于无奈,张学良邀请好友高崇民赴陕来完成这一任务。高崇民根据张的指示,“见杨时披肝沥胆,说明张之苦心孤诣,绝无失掉东北而企图到西北苟安之意。杨大为感动,认为高之言谈态度爽直诚恳,无当差(气习)。是日,留高午餐”,尽欢而散。为了进一步拉近关系,张学良接着与杨虎城举行秘密会谈,“以便交换意见,决定如何联共抗日,扭转蒋介石的‘剿G’政策。”当时张驻洛川,遂通知高崇民陪同杨虎城,由西安飞赴洛川。两位将军在极端缜密的商谈以后,确定了不打内战、联共抗日、与共产党红军三方合作的意见,并由张担任劝蒋,放弃所谓“安内攘外的政策”。为了避免蒋介石忌恨,张、杨确立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就是说暗里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下层可以让他们闹些事,以麻痹国民党特务的监督与侦查。
1936年6月15日,在西安南郊王曲镇成立军官训练团,由张、杨分任正副团长,先后分三期训练军官约500人;7月,又成立由张学良任主席的抗日同志会,以团结抗日志士,培养抗日骨干为宗旨。8月,中共又派红军代表叶剑英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抗日。到1936年冬,初步形成了由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编辑 邹吉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