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访问延安红云平台,助力更有力的红色文化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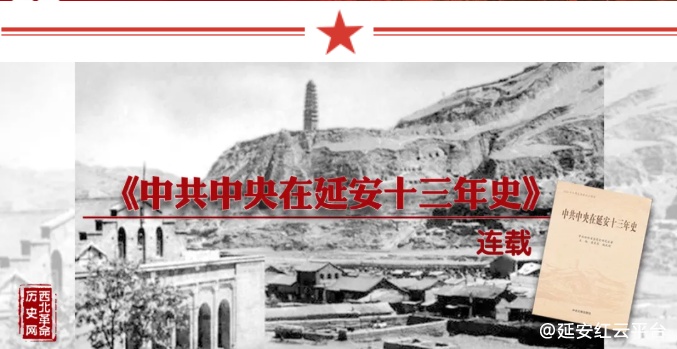
1946年1月10日,即《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全国人民期待并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38人,其中中共代表7名,即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蒋介石在开幕式致词中宣布了国民党的四项承诺:保证人民自由,各党派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致词,对国民党的四项承诺表示欢迎,指出:“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停战令,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再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提议“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
政协会议历时22天。继1月10日开幕式后,1月11日,周恩来、张群分别向大会报告停战商谈经验教训和停战商谈经过。1月12日,大会听取周恩来、邵力子关于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1月14日起,会议代表分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5个组,分别进行协商。政治协商会议上争论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和军事问题,即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关于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党代表首先提出一个《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其所谓“扩大”政府,就是在原来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中增加几个名额而已。国民党这一提案,实际上是想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对此,中共、民主同盟和一部分无党派代表表示坚决反对。会议最终否定了国民党的提案,达成了《政府组织案》,规定: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不但对方针、大计有决策之权,并有对高级官员的任免权;国民政府委员40人,国民党和非国民党各占半数,否定了国民党“特定多数”的主张;各党派的国民政府委员人选,由各党派自行提名;在议事程序上,提案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会议人数之三分之二的赞成,始得形成决议。
关于施政纲领问题,讨论施政纲领问题。中共代表首先提出一个《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但是,国民党和青年党代表却极力主张应以《抗战建国纲领》为蓝本。民主同盟代表对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表示赞同,对国民党代表以《抗战建国纲领》为蓝本的主张给以否定。在中共和民主同盟的努力下,会议最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这个纲领在内容上虽然与中共的主张有很大距离,但它确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确定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的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的途径,确定了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
关于军事问题,重点讨论整编军队的原则和办法。国民党坚持中共的军队必须编入国军,成为国军的一部分,接受“国家”统一的军令。中间势力主张国共双方都把军队交出来。希望中共在军事上做些让步,国民党在政治上做些让步,由他们出来代表国家,接受双方的军队。中共主张,“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因此,中共主张要使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国家民主化;要整编全国军队,首先整编庞大的国民党军,使其成为人民的军队。简言之,解决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方案是国民党军与解放区军队同时交给民主的联合政府。经过一场复杂的斗争,政协会议达成的军事协议,规定了“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整军办法;并确定了由军事三人小组继续商谈整编具体事项。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以及以顾问身份参加的马歇尔三人组成。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旧“国大”代表(即1936年由国民党包办“选举”产生的代表)有效无效的问题。国民党坚持旧国大代表继续有效,目的在于企图控制国民大会,使之成为将来推翻政协决议的合法表决机器,重新复活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中共、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代表都表示坚决反对。中共坚决主张重新选举国大代表,重新制定国民大会的组织法、选举法,以便召开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和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和其他绝大多数代表主张重新选举,因而使政协陷入僵局,会议被迫三度延期。为了打破僵局使会议继续进行,中共和民主同盟取一致立场,作出适当的让步。最后达成协议,在保留原来选出1200名代表之外,补选850名(民主派和解放区)新代表,并规定“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这样就改变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情况,保证了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否决权。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坚持实行1936年5月5日通过的由他们一手包办的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这个宪草所确定的是中央集权制和总统制,实质上是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个人独裁制,这样的宪法草案,全国人民当然不能承认。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提案,主张重新制定宪法草案。民主同盟和其他党派代表,对国民党的提案也表示反对,但他们所提的主张,基本上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中共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一个幻想,但考虑到要使同盟者认识到这个真理,需要通过他们的实践。同时考虑在当时就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同新民主主义制度有很大差距,但它比起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而,中共决定赞成民主同盟的主张。经过一番争论,政协会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决议案达成协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原则。
中共中央高度关注政协会议的进程。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政协斗争问题给中共代表团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改组政府方案,仍是露骨的要保持一党专政,我们不能接受。改组政府必须坚持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一切民主分子参加一切机构,公平有效的代表权),必须坚持破坏独裁,不许多数党在政府中超过三分之一。”“改组政府未协议前,对国民大会不要让步。”对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应明白表示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对此问题我们应坚决转入主动,广泛发动舆论指出国民党的庞大军队是中国军队不国家化的基本关键,必须首先要他彻底国家化,要各党派无党派共同管理军委、军令、军政、军需、军校、军队,不许排斥异党。”国民党“不接受我之要求不要紧,不会破裂,他唯一的内战法宝已受约束”,如果“我现迁就他,而参加政府,交出军队,则我有受严重约束和损失的危险”,“现先做到停战与逼他实现诺言,不要希望在政协解决更多的问题,让其拖下去,拖之责在他不在我。他现利于速决不利于拖,愈拖我愈强他愈困难被动。三国干涉可能到来,在现时国际(三国协议)国内(内战停止)条件下,他最后仍不能不实行民主。我应说服中间派了解此点,争取其共同行动,并应公开指明蒋的两面政策,以教育人民”。指示信对于中共代表在政协谈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月27日,随着政治协商会议主要内容协商的完成,周恩来和陆定一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停战、政协等问题的谈判情况汇报:“解放区问题,我们把它放在和平建国纲领中作为一般的地方自治问题,这样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打破了国民党的‘割据’之说。军队国家化问题,我们提出与政治民主化平行解决,承认军事三人小组,击破CC派先取消中共军队之说。国民大会问题,我们坚持宪章的民主原则。这些意见都取得了民主同盟的同意和合作。军事三人小组负责整编全国军队,国民党口头同意我编成二十个师,经过力争定为统一整编。我们要求改组政府实现三三制,国民党同意我党和民盟共有三分之一的名额(合十四名),可以保证行使否决权。”“会议认为:我们从抗战结束就是和平方针,但前一段的自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方针都是正确的。”1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初步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人员名单: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停战、三人会议、政协会议等情况的汇报。周恩来在汇报中说:“国大代表名额,已商定中共和民主同盟共占四分之一,保证否决权。指出几个月的自卫战争有成果,有国际影响,又教训了国民党,因而才有杜鲁门声明、三国外长公告和马歇尔来华。报告中共参加政府的名单,并说将来我党参加政府时,中央要考虑搬迁问题。”“会议同意代表团商订的政协会议各项文件,委托代表团签字。”
1月31日,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下,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决议案,随即宣布政协会议闭幕。在政协会议闭幕的致辞中,周恩来指出,会议通过各项协议,证明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在22天协商中,终于使我们这些具有长期性的历史性的许多问题,得到了政治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和各党派一起,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继重庆谈判后中国政治生活中又一件大事。政协会议各项协议的通过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按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蒋虽不愿承认联合政府这名词,但实际上如翻成英文,还是联合政府,当然这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如照政协做下去,则是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政协会议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实际。
(编辑 邹吉钧)